
近些年来,“创新”恐怕是中国人最常听到的“大词”之一,在社会的不同角落,都在谈“创新”,而中国人是否缺乏“创新精神”,也是人们争论和焦虑的中心。客观地说,这并不只是空喊口号的无用功,至少从多项指标来衡量,中国确实在进步: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评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5年中国排名第29,但去年已飙升至第17,在排名前30的国家里上升速度首屈一指,甚至超过了以色列(从第22升至第11)。

这主要得益于这些年来中国对科研经费和人才培养的大力投入,这使得中国的科技论文数量已连续十年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不过,科技创新比较容易被量化评估,但在管理、艺术、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却更深入社会肌理,推动创新也更难——事实上,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思维定势仍然在阻碍着人们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创造性,十四亿人的大脑仍有无穷的潜力未能善尽其用。
倒逼出来的创新
中国社会的创新有一个问题:其驱动力似乎往往源自外部。如果问问人为何创新,得到的答复多是:竞争激烈,生存所迫;制度环境如此,不挖空心思创新甚至申不到项目经费;如今什么都得谈创新,这总比固守不变要安全。当然,很多人创新是为了获致物质上的成功,但那最终也是指向外部的成功——很少听到有人和我说过,那是因为他从中得到乐趣。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社会的“创新”就像以前说的“进步”一样,是一股不可抗拒将人裹挟在其中的力量,它给人施加巨大的压力,这并非自由选择、让人从中感到自发乐趣、并自行承担风险、最终获得回报的事物,人们考虑的重点往往也不是“创新能给人带来什么”,而是它“能给我带来什么”。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倒逼出来的创新”——因为面临的压力如此之大,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这随之带来两个挥之不去的特性,一是强烈的目的性,二是高度的紧迫感,而这都可归结于一种“追赶”的心态。中国近些年突飞猛进的势头与此密切相关,但也正因为这样,又带来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副作用。
由于创新本身是一种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那么,之所以鼓励创新,是因为“创新带来的好处”,而不是真正喜欢创新本身。换言之,人们不是享受创新本身,而是看到了创新的功利性结果。这就跟读书一样,鼓励读书,是因为看到高学历能带来的名利地位,但不是喜欢读书本身。在现实中,不难发现很多中国人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其行为、决策,都隐含着对未来的判断,越重大的越是如此,所有的创新、变化、折腾,归根结底都要有助于这个特定目的的实现。国内的很多论文也隐藏着这样的思维,往往太想推求结论,以致前面案例堆砌后面判断武断,缺乏中间的推导与思维逻辑。
这其实与其说是现代理念中的“创新”(innovation),倒不如说更多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源于近代西方的“创新”对应的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线性时间观,强调的是打破既有的框框,无从生有创造新事物;但中国传统的变革,却是一种“权变”。
历史学家陈苏镇在《<春秋>与“汉道”》一书中解释得明白:“《公羊》家所谓‘权变’强调的是手段的灵活性,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义’或‘善’的目的,在不同情形下可以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这叫作‘量势立权,因事制义’。”这种“权变”强调的是手段的灵活性,但既有目的、框架都是不能改变的,甚至正是因为目的不能改变,手段才格外需要灵活务实,发挥你的创造力,无论找到什么办法,只要能达成目的即可。

这种“权变”可以让中国人飞快地适应情况的新变化,因为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但另一面,这些新办法却又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随时可能消亡。这种灵活性的权变,与“创新求变”显然是似是而非的两回事,因为其根本目的不在“创新”本身,而是因为不灵活变通就无法达成目的,最终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了。其结果,中国社会在剧烈变化时期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不断形成中”(becoming)的状况。
由于急于实现目标,一个新办法如果不能很快证明自己奏效,那很快就会被弃置一旁,另换一个。这种浮躁的心态在商业领域尤为常见,人们追求的往往是获利周期短、赚钱更快的项目。这带来一种“假创新”:号称“创新”,但其实只是急于自树新见,而缺乏与学术共同体的对话,有时不惜剽窃抄袭,甚至在遭遇质疑后仍各执己见。这在短期内非常热闹,但却眼花缭乱地不断更换,缺乏沉淀,没能留下持续的成果。

这其中倒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创新的推广速度极快。像摩拜单车的模式,其实在日本出现得更早,但多年下来也未推广,在中国却在极短时间里就成燎原之势。有时这甚至给人感觉是逼迫人们去体验新的,迅速淘汰旧的,上海的一些地铁站在安装自动充值的机器后,很快就取消了人工充值,以至于一些不会使用的老人要么被迫学会,要么只能求年轻人帮忙。肯德基在国内市场上的“强制驱逐式自助点餐”也可归入这一类。在这一点上,又一次体现出中国式创新社会急骤的特点,似乎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人更好的体验,而是迫使你跟上步伐。乔布斯曾说过,创新的顺序应该是“先想好如何满足用户的需求,其它的都会随之而来”;那国内很多企业的想法则似乎是:“先搞出一个创新,然后立刻大规模推广,软硬兼施让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至于这是不是真的改善了用户体验,则不是重点。”
在急切赶超的心态下,常常还导致不计代价地短期投入。这不仅是在工程、科研上,甚至人文学术也不例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980年代初成立时,邓广铭等各位前辈就共同制定了一项方针:“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一切都要“快”,如果是重大项目,还需要所谓“集中攻关”。问题在于,别说是人文,就算是科研、商业领域,很多事也不能太看短期的KPI,不能要求每年都比上一年增长30%,有时甚至需要很长的沉默期。
至少在文化创意领域,“集中攻关”不能带来有个性的原创,因为“攻关”本身就意味着实现“攻克”这个目标,但真正的原创,起初往往是漫无目的的,源于人性的好奇。用导弹之父布劳恩的话说:“基础研究就是:当我在做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华为CEO任正非曾说,他们在俄罗斯聘用了一个科学家,到公司十来年天天玩电脑,“管研究的人去看他,打一个招呼就完了。我给他发院士牌时,他‘嗯、嗯、嗯’就完了。他不善于打交道,十几年干什么不知道,之后突然告诉我,把2G到3G突破了,马上上海进行实验,我们就证明了,无线电上领先爱立信,然后大规模占领欧洲,用了4G、5G。”他总结说:“我们现在很厉害,与这个小伙子的突破有关。”

真正的创新往往都是这样,人们只是沉浸在其中,“想把它做出来”,但这个新事物究竟是什么样、做出来之后能有什么用处,都是未知的。事实上,历史上的很多新发明,起初都只有一些乍看最没用的用途(有人讥讽最早的电话只是让人多说了废话),甚至根本不清楚有什么用,又或者,新事物乍看还没有原有的东西好——火车最初还不如马车跑得快。此外,常有的一幕是:创新在无意中涌现,诸如微波炉、不粘锅、心脏起搏器等,都是意外的产物,最有名的大概是辉瑞公司原本研发心脏病药,结果却无意中得到了“伟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好奇心、对不确定性保持乐观,都是不可或缺的品质。
真正的学术创新源于一种内在驱动的求知欲,正如日本学者栗山茂久所强调的,这会让人不断鞭策来自我突破:“一个成熟的学者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套路,他的学术惰性也就出现了。这种学术惰性就限制了他的学术创新能力。而要有所超越,必须意识到这种学术惰性的存在。”这种品质在国内之所以匮乏,恰是因为很多人的目的不在求知本身,而是学术带来的名利、资源等,所以创新对他们来说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既然已经功成名就、目的达成,为何还要努力刷新自我?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难道创新就不用看绩效吗?当然需要看,现代的创新早已不只是个人玩得开心而已,尤其是重大突破,往往都需要密集资金投入和团队合作,也不可能漫无边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创新本身需要相当大的自主性,甚至一定程度的“失控”。目标太明确的人,也许能很快实现目标,但他却很难超越目标,收获意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的创造力仅仅源于外在压力,而非由内在驱动,那么他很可能会疲于应对外界瞬息万变的情况,甚至茫无所从,难以长期专注于一点,但在创造性活动中,“长期专注”可能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突破都来自于对前沿领域长久的深入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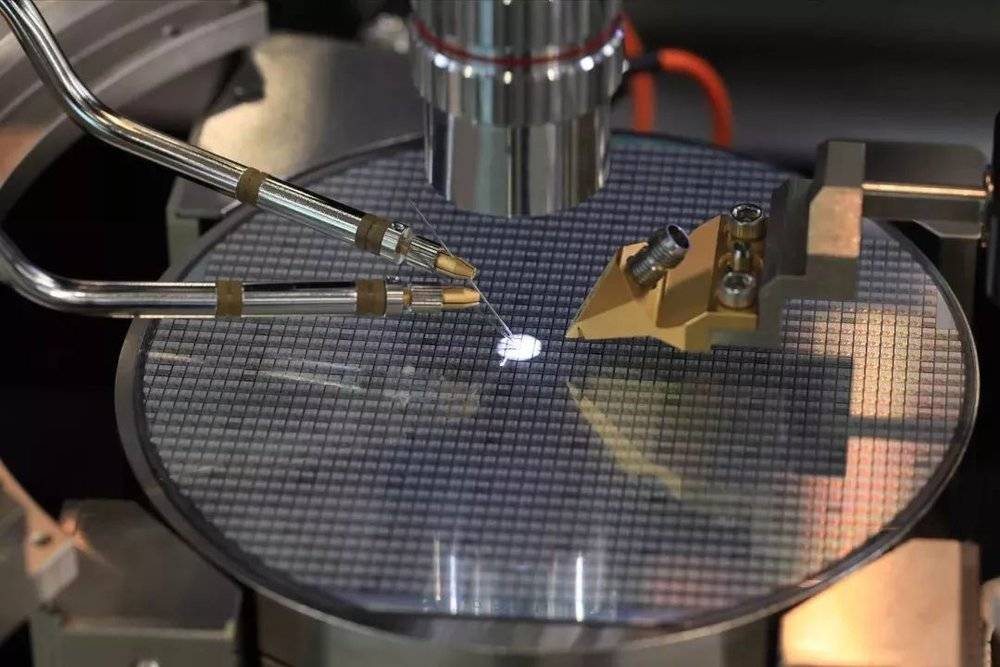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以前还可以说“需求带来创新”,但现在则往往更多的是“创新带来需求”——所以乔布斯曾说他不需要市场调研,因为如果问马车时代的消费者,他们只会说想要更快的马车,而想不出汽车是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创造出来,人们才知道自己需要。这凸显出一个真谛:到了最前沿,创新是不能靠外力推动的,而只能依靠内在驱动的创造力。
创新即是变革
以往的很多讨论,似乎都以为创新是某个天才的想法,又或者是投入产出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意味着社会形态和思维方式脱胎换骨的变革。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不是一个概率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毫无疑问,十四亿人中并不缺乏创新的人才,但创新并不会从人群中自然诞生,因为某种程度上,它就像娇贵的珍稀动物,只在最适宜自己生长的特定环境下才能有蓬勃生机。没有一定的制度保障,零散的资本、人才、想法就很难聚拢成一个丰富复杂的生态,并最终达到催生创造性突破的临界规模。
在《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一书中,着重指出了一点:单凭伟大而专注的头脑不足以造成创造性突破,否则西欧文明绝无可能在1450-1550年间超越中国。个体天才的数量在不同社会的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体并无差异,因此明代中国原本聪明头脑几乎是西欧的两倍,还抢占了技术上的先机,但欧洲的靠的是“集体天才”(collective genius),也就是说,当时西欧社会活跃的公共空间提供了充分的交流互动,使不同的头脑致力于同样的问题,并激发出原创性观点。基于此,该书提出集体天才的三大条件:思想流动的速度、种类和丰富程度的暴涨;对思想交流的参与性;以及私人和社会对冒险行为的慷慨激励和回报。如果创新得不到鼓励和回报,那它很容易熄灭。

哥白尼像
社会的大规模创新本身就需要持续不断的思维更新和大量投入,因而卡伦·阿姆斯特朗曾说:“在所有的前现代社会中(包括农业时期的欧洲),教育是设计成用来阻止个人的创新和好奇,因为对于一个没有能力吸收或运用新鲜观念的社会,创新只会破坏社会安定。”在这样的社会里,新思想就是异端,“创新”和“渎神”几乎是同义词。历史学家马歇尔·哈济生提炼出传统社会抑制改变的两个原因:“新风格在被接受之初通常都相当粗野,以及特别在以农耕为基础的经济当中,容许实验性作法的空间相当狭小。在某些情形下,这两个理由都能造成文化发展的严重阻碍。”简单来说,“新”不必然“好”,因此要给它可以存活的空间,特别是容许试错、不断改进。
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落到现实中,却不见得能被人广为接受。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异端,尤其是艺术上的创新,几乎就是靠不断挑战主流、否定自我来获得前进的,这种“创造性破坏”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在动力。但在一个把差异视为偏离、错误和低劣的社会里,创新的处境是很艰难的;既要符合主流、又要创新,这可谓中国式的“对立统一”。
阻碍中国人创新的另一个巨大束缚是“怕犯错”,这可能是社会普遍心态的产物。一个新的想法当然不必然是对的,但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似乎总期望“新”的得是“对”的,如果它挑战了常理或确实被验证为错的,那么提出这个创新的人就要倒霉了,轻则遭遇讥讽,重则以此作为衡量他水平的标尺,以至于他此前的成绩都不重要了,常说的一句就是“他连某某都犯错,水平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但人毕竟不是神,就算出错也没什么,何妨拿出来讨论下?实际上,对新事物的担忧、嘲讽、打击,是每个社会中抵制创新时最常有的表现。
正因此,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发现,“那些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经常成为不需要太多资本的主动创新者。这也并不奇怪,如果贫困人口现在的实践都是失败的,那么赌一把往往是有意义的。”(《国家的视角》)这就像晚清时中国出现了各种新思潮,因为反正情况已经不能再坏了,那么任何新尝试都不妨拿来试试,兴许其中就有哪个能奏效。如果说在一个多元的的组织和社会中,创新的机会比较多,那恐怕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组织结构里,新观念存活的机会较高。

如今,中国人都清楚创新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驱动力,它因而被广泛视为一件“好事”。不过,人们在有意无意中仍然为它设下了种种限制,与此同时又不切实际地期望一个创新的“点子”就能带来神奇的效果。然而,现代的创新早已不是零散自发的“灵感”,它需要的是制度化的保障。这又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意味着鼓励能够有效探索新知识的人才,为此全新的社会组织就要将创新加以制度化:提供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业和试验、放开竞争,总之,创造一个有助于激发个人主动性的环境。
现代精神的核心是创新、是冒险、是自发,缺乏这些的社会必然会落伍。给时代创新者的创新予以有保障的回报,才能充分发挥出他们的能动性。
历史也表明,保守的态度并不一定排除创新:像火车在英国出现时,社会各阶层都曾反对“魔鬼一样的火车头”;关键点在于:如果反对的声音并不是扼杀创新,那么这种忧虑也是合理甚至健康的,因为缺乏制衡的创新确实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正确的做法或许是“摸着石头过河”。
两百年前,托克维尔在深入观察美国后曾说,美国社会存在某些潜在致命缺陷,其中最明显的是有变化而无发展,这阻碍了创新,无力将变化转变为进步。这话出自公认最了解早期美国的学者之口,在如今看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考虑到当时的美国还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这也可以理解。这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创新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但只有在这个社会的制度保障、思维变革到位之后,一个真正的“创新型社会”才会随之到来。
 iNews新知科技 关注科技,自有新知
iNews新知科技 关注科技,自有新知

